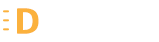格列佛游记好句好段摘抄通用3篇
《格列佛游记》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又译为江奈生·斯威夫特)创作的一部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相信亦有很多人都看过,以下是爱岗的小编帮大伙儿整编的3篇格列佛游记好句好段摘抄,仅供参考。
格列佛游记摘抄 篇1
关键词:唐代;书手;墨迹特征
唐代的书手来源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既有任职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的“楷书”、“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更有佣书于民间的贫寒文人、经生等等。他们的书写大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格式或规律进行,其墨迹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经文的缮写,更有着平实随意的日常实用性书写,展现出不同于时代潮流之上名家书法的特殊一面,他们的书法活动虽然默默无闻,却是唐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书手墨迹的书体多样,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在内的几乎所有书体形式,而且还有篆楷、隶楷、隶草相互杂糅的抄本,样式丰富。从书写功用来看,书手以抄写文献典籍、宗教经文以及重要公文为主,因此楷书是书手最常用的字体。
楷书发展到隋唐,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也在艺术上达到它发展的高峰。即使是今天,学习楷书的人仍以7世纪的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到8世纪的颜真卿(709—785)的作品为范本。隋唐时期对于楷书的定型,几乎达到完美的程度。在当时,楷书的繁盛是整体状况,众多的从事实用性书写的书手在官方和民间从事抄写活动,共同推动了楷书在唐代的繁荣。
唐代书学教育十分发达,其基本原则,是以“楷书正样”为终极目标,所谓“楷书字体,皆得正样”,[1]如《干禄字书》即是教导书写者如何学习工整的楷书以取功名,这是“干禄”的本意。唐代科举以书取士有三种方式,一是贡举中的书科;二是吏部铨选之身言书判;三是制举之科的书判拔萃。《新唐书·选举志》云:“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2]就是说,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员不须参加书判考试,六品及六品以下要参加考试,程序是先观其书判,再察其身言,然后拟官。“书判拔萃”乃吏部铨试选人特殊之法。洪迈《容斋随笔》载:“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3]虽然以书取士仅仅是在制度上的规定,在选官过程中并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但毕竟反映出书法在唐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这样说,唐代是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最终导致了官楷的形成。这样规范的楷书点画运用多了,必然强调出一种法度,对点画作一种规范的追求。唐代书手抄写活动主要是缮写图书经籍、佛经道藏等等,其书迹必然以“皆得正样”的楷书为主,其中以写经为最。这与佛教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自西晋时,写经卷便已粗具经卷体的规模。写经小楷从魏晋开始,是作为传播教义、培养出家人研读书写的一种形式。而至南朝时,字体益趋端整,楷法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去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但在写经上已无此分别了;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当时这种美观而且实用性极强的字体,被称为“官楷”,也被称为“端楷”,而写经体又是官楷之一种样式。楷书在唐代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楷法的成熟与完善,唐人将楷书推向了极致。敦煌写经中即有诸多书手抄写的端严方整的经卷,如《妙法莲华经》题记:斯84号、斯312号、斯456号、斯2573号、斯3348号、斯3079号、斯4209号、斯4551号、斯5319号、伯2195号、伯2644号、伯4556号、北新637号……共三十五号,皆为高宗时期的官府书手写本。这些经卷校勘精细,书写优美,被当时社会视为上品,深受寺院僧侣和信士的欢迎和信赖。
书手供职于官府或民间的写经坊,皆奉当时名家之书体为楷模,间或有酷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楷书,功力较为深厚,其书风既继承了前期经书的质朴,又显示了唐楷特有的典雅、稳健,笔法圆融遒丽,外柔而内刚。总的来说,尽管他们达不到虞世南、欧阳询那样高超的水平,但作为当时的一流书手还是名副其实的。可以看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强大的国家监管造就了唐代书手抄写的独特风格。他们或师承当时一流的书家,或有严格的训练作为保证,在便捷抄写的需求下,形成了以楷书尤其是小楷为主的书写特点。
另外还有一种近似行书形态的楷书,其结体疏朗舒展,一笔一划并无连带,属楷书范畴,多见于宗教以外的儒家典籍写卷,唐代中、后期,这种类型的楷书逐渐增多。如:伯25lO号《论语》、伯2540号《春秋经传集解》、伯3847号《景教三威蒙度赞》、伯2155号《曹元中状》、伯2486号《春秋谷梁传哀公》第十二等。此类典籍的抄写并非一味方饬端正,具有行笔轻快、流水行云、飘逸自如的特点,有明显的行书体势和速度感。这种楷书较端严整饬的官方抄经更加俊秀有活力,不拘束,时有书卷气息。
总之,从字体的角度分析,书手在学习阶段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字体,《唐六典》载:“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两年,字林一年”,[4]这是唐政府对馆学书手的学业规定。其所学字体至少有古文、篆书、隶书、楷书四体,其他书手学书过程基本一致,但是在学有所成之后,成为一名书手从事抄书、抄经一职,因其职业性质所限,主要以楷书、尤其是小楷书为主。
二
唐代经文典籍的抄写大都严肃而认真,尤其是官府还设立专门机构,并派专人管理,监督此事。抄写有一定的程式和工作规范。整个抄写工作分解为若干环节,由专人分别负责。其抄写主要由书写技艺高超的楷书手、群书手、官经生等承担,用工整、熟练的楷书抄写在1尺×1.5尺或1尺×2尺的上等厚麻纸上。[5]经书正文的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经卷尾要写题记,题记一般包括抄写年代、抄写者以及校字、详阅者姓名等。经文格式的规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手抄写的规整统一的特点。正如《宣和书谱》所言:“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书名”,“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一时为流辈推许”;“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6]书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首先要保持恭虔之心,心平气和;其次,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由此形成了规整纯熟的特点。其书写既传播了宗教义理,又于潜移默化之中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普通民众的陶冶作用。
以《善见律》、《灵飞经》为例。经生国诠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写的《善见律经卷》,是一件传世的唐代著名写经小楷。根据杨仁恺对“皇姊图书”印章的研究,此件作品曾经被元世祖忽必烈的嫡亲曾孙女皇姊“鲁国大长公主”收藏过。清代又曾进入内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为乌丝栏纸本,纵22.6厘米,横468.8厘米,共274行,4000余字。
抄写者国诠,是唐代贞观年间的经生,奉敕用硬黄纸本书《善见律》,经卷末后注诸臣,有阎立本署名。其书清晰可见贞观年间楷书之精熟,亦能领略到书手写经的技巧之娴熟、楷法之完备。此经书法运笔精熟劲健,笔画匀净,结体疏朗秀劲,结构严谨、平整、秀美,字形偏方扁、章法排列整齐。非心情平和、气顺意畅不能为之。既有欧阳询之端谨,又具备褚遂良之灵动,一气呵成,自始至终无一懈怠,极为难得。虽然是奉敕之作,但书体庄重自持,皆成一律。
传为钟绍京所书的《灵飞经》是唐人抄经在敦煌遗书之外的传本,又名《六甲灵飞经》,为道教经,没有书写者名字。《灵飞经》墨迹本现存43行,共计625字。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所作。玉真公主敕写。自《灵飞经》问世以来,一直为书家所推重,被视为是小楷的典范。它的用笔与字形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结字特征具有典型的规范性,是正统帖学精美一路的代表作。此经用笔以中锋为主、偏锋辅之的外拓法。帖中每字的笔画都有重笔和轻笔,起止分明,笔画柔中有刚,刚柔互济。章法上错落有致,妙趣横生。它以点代画之处较多,使间架宽绰,如“清”、“飞”等字的处理,既开阔了字的空白处,也起到密中见疏的艺术效果。在很多字的处理上,都强调主笔的突出,增强笔画间的对比效果,如:“行”、“晏”、“甚”、“五”、“真”等字的处理,使得字的结体开阔、舒展。可以说《灵飞经》秀美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都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表达无余。
上述两种写经,在总体面貌上存有一些相似性,如字形的方整、竖笔和捺笔的重压等。时代相近的写卷,师承同流的写本,许多字的“写法”也会具有“一致性”。后设立的写经所的书风,尽管时代只隔了几年或十几年,但却可能有与前一个写经大致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在现传的写经卷子中即可找到这种风格具有相似性的墨迹。唐上元三年(762)书手程君度写的《金刚般若经》,与国诠的《善见律经卷》,有着更大的相似性。甚至有些作品几乎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也就不奇怪了。在敦煌的写经卷子中,写于高宗仪凤元年(676)的官写本《金刚般若经残卷》(伯3278号),用笔精劲,笔画圆活,俯仰抑扬,提按波挑都体现了书手良好的书法素养。在官方写经中,这样的作品相当多,呈现出规整、统一的风貌。如:唐贞观廿二年(648)郗玄爽写《佛地经》、唐龙朔二年(662),经生沈弘写《阿毗昙毗婆沙卷第五十二》、唐龙朔三年(663),皇甫智岌写《春秋谷梁传桓公第二》、唐上元三年(676),书手程君度写《金刚般若经》、唐上元三年(676),书手袁元写《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唐仪凤元年(676),书手刘弘珪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7]……
每一件书手墨迹所呈现出的规整精熟的风貌,与当时书手的劳役以及与所接受到的技艺教育、培训密切相关。书手的抄写之役,类似工匠番役,须上番、积劳累考,须遵循官府制定的规范样式。经过行之有效的技艺训练后,达到端正整肃的水平。由于抄写的需要,美观大方、工整不潦草是首要的标准,而且由于大量抄写的需要,熟练又是同样必须做到的。这既需锤炼的工夫,又需练习的技巧。如在写经机构中,师承制是最普通的技艺传递方式。年轻的书手们往往从师于同一位师傅,他们使用的纸、笔等工具也很可能是共同配置的,因此显示出极为明显的相似性。再者从笔迹学的角度来讲,书写者长期从事“重复性”的抄写,书写动作很熟练,手势习惯会变得相当定型。所以,凡一人所抄的卷子,笔画、偏旁部件、结体方式等的“写法”比较统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兼顾书迹端正与书写快捷的情况下,书写者容易流露出自己比较固定的书写习惯。
三
书手这些具有规整纯熟特点的墨迹互相对比时,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同是楷书墨迹,《春秋谷梁传集解》(伯2570号)作横势而饶有拙趣;《古文尚书卷第五残卷》(伯2643号)则挺拔劲爽;《玄言新记明老部》(伯2462号),颇有禇遂良刚健婀娜之笔意;《汉书萧望之传残卷》(伯2485号),可与杨凝式《韭花帖》相颉颃;《阅紫录仪》(伯2457号)则开启苏轼楷书的法门。而诸如《老子道德经卷上》(伯3725号)、《道德经序诀》(伯2596号)等等楷法极精、资致遒妍的佳作,甚至当作楷书法帖也毫不逊色。[8]
书手技艺的传承,或者师徒相授,或者风习相染,在他们的笔下总有一脉相承的基调。但是“技”与“道”之间并无严格而僵硬的划分,无论是写自西陲,还是写自中原,抑或是写自江南,都会有相同的形质特征,但与作为“艺术”的书法无论是在功用上还是在风格上,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书手的写卷墨迹尽管在同一时期,其书法风格,也可能是差别迥异的。尤其是书手会因其师承的延续性而保留前代的一些写法(书写之法与文字结构之法),同时又受到时风的感染而发生一些变通。就风格来说,出现一些与当时所流行的书风不尽一致的面貌是很正常的事,如同样是书写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的《大菩萨藏经卷三》[9]写本上,体现出的竟然还是一种魏碑样式。
此卷抄于贞观二十二年。据载,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返抵长安,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同年五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这是翻译三年后由官府抄写完成的抄本,题记中说明了是由当时重臣许敬宗(592—672)监阅的,体现了政府支持与参与的严肃性。抄写当然也是由官府训练过的书手完成的,可这宗卷子上呈现出的魏碑风格非常显著,表现在笔力、用笔和结体上,如“八”、“又”捺的重按尤其在“口”、“田”、“日”等部首转折处方硬的折角是其他小楷抄经所见不到的,这既有书手个人的因素,也反映了书法风格变化的不同一性。
除了官方书手之外,大量的非官方的、民间的抄经和日常应用大都由民间书手来完成。纸写书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书籍装潢的改进,得以高速发展。抄书促使新的职业诞生,被称为书手的文人,下在城坊、学校、寺院以抄书写经谋生,上在朝廷、官府供职,一大批民间抄本图书经卷便应运而生。从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出,这些写经显然不是以个人使用为目的,而是为了投入市场以换取粮米或银钱,当时的抄书已不是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成为一支队伍的集体劳动。
敦煌遗书中存在不少充满奇趣的书手书写墨迹,大都为非官方、非政府的民间写经,它们同样体现了书法史的变迁。斯2424号李奉裕写《阿弥陀经》题记云:“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邓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这件经书,可以初步断定是民间书手所为。原因有三:一是书手将抄写作为一项赖以谋生的工作,很辛苦。即使是受到大量专门训练后的抄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体力活,而不是优游其间的雅事。在唐朝当时以抄写经书来“自娱”是不合乎实情的,他们受到职业的限制,全力以赴地工作尚可安身,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别的抄写。二是“在家未时写”即说明不是为官府进行抄写。这显然不是官府职业书手在为自己家里颂佛抄经,而只是一个处身民间的普通书手的一种劳作形式。从其中相对较多的涂改就能看出,抄写明显带有随意的成分,不似官方抄写的一丝不苟。在当时佞佛诵经相当虔诚的世风下,官方抄经是不允许有这样的成品出现的。另外,此经书也没有诸如上述经书那么多严格的校订程序、众多的审查人员。从其运笔来看,虽然书写时不加雕饰使得笔力有羸弱之感,与前面所叙及的《善见律经卷》与《灵飞经》不无差距,但正是这种不讲究用笔技巧的书写,较之官府书手端严肃穆的抄写别有一番活泼、朴质的特点。另外,有些字甚至抄写到了经卷乌丝界栏之外,并没有对字的大小作通篇的限制。官府书手如果写到这样,恐怕是不可以的。最后,从这卷经书来看,还是能够看出抄写者受到一定的书法训练,而且时间并不会很短。其书写是流利的,字形结体开张、宽绰,显示出唐代特有的一种爽朗、磊落的风神。这显然不是出自一个随意找来的人的手笔,而是一个民间书手的“产品”。景龙三年(709),欧、虞等书家离世已有几十年。此后的几十年,正是颜真卿的时代。初唐宽博、大气的楷书风范已经逐渐形成,并在播及到民间。这卷《阿弥陀经》,就是这一时期民间书法的最好反映。再如索慎言所抄《无量寿宗要经》,也显示出不同的风貌。“觉”字最后一笔鹅浮钩,与唐贞观廿二年(648年)郗玄爽写的《佛地经》(伯3709号)[10]中的钩拐弯直上向内挑的写法完全一致,这是对一种样式的学习造成的,不是一个毫无书写训练的人偶然写出来的。且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这种写法的技巧,但至少说明这是一种样式或是流行的风格。图示部分出现了几次的“定”和“正”字,其结构和用笔都是无可挑剔的,整个经卷笔法娴熟,结体紧凑,笔势连贯,虽不如正规抄经的匀整静气,但多了一些活泼自在和个性化的成分。这也说明了这位抄写者具有一定的功力。
尽管这一类型的书手,在抄写过程中不怎么留意用笔的点画、结体、章法等法则,往往是信手抄来,不加雕饰,却又错落有致,笔意间流露出一种拙朴的美。虽然他们的书写技巧远不能与技艺高超的御书手、楷书手相比,但他们奇趣自然的书写也构成了书法多样性的一面。
四、结论
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欧阳询、虞世南、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为代表的名家作品,美不胜收,传写不衰。这些流传至今的名家墨迹都是经过历史筛选的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东西,它们体现了当时书法发展的主要潮流和主要贡献,但是并不能代表当时书法发展的总体面貌。一个时代的书法水平如何,既要关注所谓的精英、大家,也要看社会总体水平。所以,唐代书法的繁荣昌盛,固然首先要重视那些载于史册的书法家,但也不能忽视名不见经传的书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为书写者个体,学习书法方式的差异、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使得书手的书法亦具备了率真奇趣、丰富多彩的风貌。不仅如此,书手在长期实用性书写过程中,甚至形成了某种特定的风格流派,影响了一代书风,如“经生体”、如“官楷”。充分肯定书手墨迹其不容忽视的书法价值,对于了解唐代书法的真实状况以及书法时代变迁的基本脉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溥。唐会要[M].卷七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659页。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Z].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1171-1172页。
[3]洪迈。容斋随笔。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27页。
[4]李林甫。唐六典[M].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562页。
[5]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41页。
[6]宣和书谱[M].卷五。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92页、103页。
[7]法藏敦煌书苑精华[A].第六册。写经(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1—195、213—218、219—222、225—234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是书未公开发行。
[8]参见刘涛。《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J].书法研究。1998年第3期。
格列佛游记摘抄 篇2
书是一阵风,吹散烦恼乌云;书是一阵雨,滋润心灵成长;书是一声雷,惊醒恶梦回头;书是一丝光,指引前进方向。世界读书日,愿书伴你快乐一生。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生必读名著,供大家参考。
高中生必读名著1、《西游记》吴承恩
2、《水浒》施耐庵
3、《朝花夕拾》鲁
迅
4、《骆驼祥子》老
舍
5、《繁星·春水》冰心
6、《鲁滨孙漂
流记》(英)笛福
7、《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
8、《名人传》(法)罗曼·罗兰
9、《童年》(俄)高尔基
1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格列佛游记摘抄 篇3
17世纪中叶,漠南蒙古归附清朝以后,蒙古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四卫拉特联盟和喀尔喀蒙古地区。为了反对沙皇俄国的入侵和抵制满洲势力的扩展,加强蒙古内部的团结,卫拉特、喀尔喀蒙古统治者们,于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民族法典,在蒙古民族法制史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这部法典,继承和发展了蒙古传统法制传统,在蒙古立法史上是继成吉思汗《大扎撒》后的第二次高潮。这部法典,也曾一度影响了整个阿尔泰-通古斯语系的诸民族。噶尔丹洪台吉建立准噶尔汗国后,1676年和1678年对《蒙古-卫拉特法典》进行了两次补充,学术界称之为《噶尔丹洪台吉旨令(敕令)》。《蒙古-卫拉特法典》颁布100年后,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廷第七任汗顿罗布喇什认为,《蒙古-卫拉特法典》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应实际需要,故而于1741—1758年间对《蒙古-卫拉特法典》进行修订和补充,约有50余条,学界称作《顿罗布喇什补则》。
一、法典颁布前的卫拉特社会状况
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是oyirad的汉语音译。元代时将其译作“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外剌歹”等。明朝译作“瓦剌”。清朝至今,汉文史籍中常译作“卫拉特”。亦有译写为“额鲁特”、“厄鲁特”,或称之为“西蒙古”者也有之。厄鲁特或额鲁特只不过是卫拉特蒙古诸部落中古老的部落之一ǒgeled的汉语音译,清代有些文献中常把厄鲁特、额鲁特来指称整个卫拉特,这是不确切的称呼。西蒙古是相对东蒙古而言。而外国一些著作还往往将卫拉特称之为“卡尔梅克”(kalmuk/kalmyk)。
卫拉特先民斡亦剌是《蒙古秘史》所记载的“槐因亦儿坚”(oi-yin-irgen),即“林木中百姓”中的一个森林部落。居住在谦河(今叶尼赛河上游)一带,操蒙古语,以狩猎为主,也进行畜牧业、采集和捕鱼。他们“人数众多,分为许多分支,各支各有某个名称”。(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193页。)13世纪初归附成吉思汗并建立联姻关系。当时“林木中百姓”在行政上分成四千户,成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地。后来拖雷夫人梭鲁禾忒尼将自己在阿尔泰山和兀良罕、吉利吉思地区的领地让给其子阿里不哥后,成为阿里不哥属民。元朝1307年建立岭北行省后,归岭北行省管辖。
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初阿里不哥、海笃等叛乱时,斡亦剌部一部分站在叛乱者一方西迁,一部分从叶尼赛河上游迁到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元廷北迁后,因明蒙战争和蒙古内讧,很多蒙古部众为躲避战乱,来到斡亦剌等森林部落中杂居。(注:伦布彻林著:《蒙古布里雅特史》(托忒文)。) 直到公元1500年,外剌统治集团处处维护蒙古大汗的利益。随着蒙古大汗为首的黄金家族权威的旁落,异姓贵族阶层的势力逐渐强盛。明朝永乐皇帝初年,外剌和蒙古本部分裂。经过外剌妥欢太师和也先太师父子经营,外剌势力达到鼎盛时期,时常威胁明朝和蒙古各部。1453年(明景泰四年)也先统一蒙古诸部,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建号添元(天元)。1454年,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先汗被杀,从此外剌势力日趋衰微。其后经过东蒙古达延汗和土默特万户阿勒坛汗屡次兴兵征讨的结果,外剌部被迫逐渐西迁。
16世纪初,外剌的主要活动地区东至坤奎、札布罕河以东的哈喇和林一带,西连额尔齐斯河,北至唐努山,南抵察合台后裔诸王的领地。16世纪中叶,兀良罕万户在漠南蒙古阿勒坛汗等封建主的六次征讨下瓦解后,喀尔喀万户格埒森扎后裔向西发展,占据兀良罕万户地,进而不断向西推进,占据卫拉特所属的坤奎、札布罕河流域以及唐努山、萨彦岭一带的牧场。卫拉特被迫迁居到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上游以及叶尼赛河上游地区游牧。从此以后,卫拉特和喀尔喀右翼之间的矛盾不断升华,互动干戈,时战时和,直到17世纪中叶共同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为止。
关于卫拉特联盟的形成时间以及各个阶段组成部分的变化,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此不赘述。据巴图尔乌巴什图们著的《四卫拉特史》、噶旺沙拉布著的《四卫拉特史》、无名氏著《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诸汗史》等托忒文文献和蒙汉文史籍对比研究,卫拉特似曾有过三次程度不同的联盟。大约1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看似松散,实际上相当稳固的联盟形成了。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一联盟的形式更加明显。此时的成员包括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辉特、额鲁特、巴噶图特等部。其中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最强,习惯上以“四卫拉特”(durben-oyirad)来概称卫拉特各部。
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组织主要由兀鲁思、鄂托克、昂吉、集赛、爱玛克、阿寅勒、和屯来组成。
15世纪后半期以后卫拉特社会逐渐出现了鄂托克这一社会组织,由若干鄂托克组成兀鲁思,从而代替了蒙元时期的万户、千户组织。
17世纪初,黄教传入卫拉特地区后,出现了专门管理宗教事宜的机构——集赛(jisa)。“初为五集赛,后增其四,成九集赛,亦领以宰桑,略如鄂托克之制”。(注:《西域图志》,卷29,官制一。)
爱玛克是彼此又亲族关系的家族集团。游牧于同一地区(努图克)的同族阿寅勒集团称之为爱玛克,它是近亲家属的结合,是由渊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人们结合而成。在东蒙古,爱玛克的组织比较明确。几个爱玛克可以组成一个鄂托克,或者大爱玛克可以单独组成一个鄂托克。鄂托克与爱玛克的区别仅仅是有无血缘关系上。而阿寅勒是组成爱玛克的最基本的单位,阿寅勒是同姓或近亲组成的同一个努图克上游牧的,以禹儿惕(帐幕、蒙古包)为核心的蒙古社会最小生产单位。他们以和屯的方式游牧。“卫拉特人的这种和屯是以长老(阿哈aha,即哥哥,一般指某一群体中的年龄最大的人或有威信的人)为首领的共同宿营的和共同游牧的氏族的一部分或近亲集团”。(注:《蒙古社会制度史》,第266页。)也就是由相近血统关系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游牧和管理事务的家庭集团。
所以,卫拉特联盟的社会组织是兀鲁思-鄂托克(昂吉)-爱玛克-阿寅勒(和屯)来组成。(注:有关鄂托克、昂吉、集赛的详细情况参见《西域图志》外,还可以参考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63页,《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267-273,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卫拉特历史文献》第131-133。)兀鲁思、鄂托克的诺颜们进行楚勒干决定卫拉特联盟内外事宜。
卫拉特联盟从社会阶级结构上来看,由诺颜阶层和阿拉特阶层组成。从《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条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情况。世俗封建领主由汗、珲台吉、台吉、宰桑、图什墨尔、扎尔固齐、德墨齐、阿尔巴齐宰桑、收楞额、阿尔班尼阿哈等大小封建主。宗教封建主由呼图克图、大喇嘛、陀音等。庶民阶层按其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不同而分若干阶层。大致分为阿拉特、哈喇出、哈喇里克。若详细分,赛音昆(上等人)、敦达昆(中等人)、阿达克昆(贱人)、哈喇昆(一般人)、恩衮昆(平民)、称为默德勒(属下人)的家仆、奇塔特(汉人)或默德勒孛斡勒(属下奴隶)的奴隶和专门服务于寺庙的沙比纳尔(寺院属民)等不同称呼,不同性质,不同义务的阶层组成。
其中赛音昆阶层属于富人,塔布囊(驸马)、赛特(臣僚)、达尔罕(自由人)等经常从这一阶层出。敦达昆是封建领主征用实物的主要对象。阿达克昆是征用劳役的主要对象。这两个阶层是军队的主要来源。每一个阶层都对上一个阶层提供阿勒巴(贡赋和服役)的义务。由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决定阿勒巴的轻重。提供阿勒巴的人被称为阿勒巴图。从称呼上可以看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众多史料表明,封建领主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属民。在兀鲁思内的土地、牧场、牲畜等都公开和隐蔽地为领主所掌握,个体牧民有使用权而没有支配权。
卫拉特被迫西迁后,失去了相当广阔的牧场,因人口和牲畜的不断增长,带来了游牧领域相对紧张的局面。各部之间因争夺牧场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时常受到来自于喀尔喀右翼阿勒坛汗一系的威胁。为开发新的领地,求得生存与发展,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联盟首领们对内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卫拉特联盟建立了“楚勒干”(或丘尔干,qigulgan)制度。楚勒干是蒙古语会议、会盟的意思,类似于古代蒙古社会忽里勒台制度。楚勒干是贵族会议,由卫拉特各部贵族参加,共同商讨内外大政,协调内部关系,组织对外战争等事宜。
卫拉特联盟楚勒干并非常规机构,各部共同推荐一到二名强大部落首领当盟主(qigulgan-daruga)。前期一直由从东蒙古科尔沁部迁徙过来的哈撒儿后裔的和硕特部封建主担任。17世纪20-30年代,卫拉特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势力迅速增长,打破原来和硕特封建主为盟主的状态。托忒文史料记载,卫拉特联盟封建主们通过楚勒干决定,为寻求新的牧场和发展,妥善解决这一对生存带来的矛盾,1628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额尔勒克率土尔扈特大部和一部分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民,越过哈萨克草原,远徙之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紧接着卫拉特联盟首领和硕特部顾实汗1637年率领部众和部分其他部落卫拉特人占据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这时候卫拉特联盟是由和硕特部额齐尔图台吉和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共同治理时期。卫拉特联盟的领地空前的扩大,为建立准噶尔汗国奠定了基础。
前面说过,16世纪后半叶,黄教传入东蒙古地区。蒙古社会掀起了一股“政教并行”的政治改革。其主要措施之一是制定法典。因地缘的原故,西蒙古的这项改革措施比东蒙古地区较晚。但值得一提的是,1640年大法典制定前,卫拉特联盟好像有过地方法规。目前学术界所掌握的后来被称之为旧《察津毕其格》的法典的残片8条。有些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过质疑。
当时在东蒙古站住脚的西藏黄教势力也需要卫拉特的支持。于是17世纪初,卫拉特联盟封建主们,适应时代的需求,积极引进和倡导藏传佛教,消除萨满教的影响,皈依黄教,成为虔诚的佛教徒。黄教的传入起到了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内部团结,消除因争夺牧场、属民而酿成的隔阂、矛盾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著名的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从土虎年(1638年)到水虎年(1662年)的24年中,东起青海,西迄斋河(今乌拉尔河),南至裕勒都斯草原,北达额尔齐斯河流域,足迹遍及卫拉特地区,而且一度去过喀尔喀传教。(注:参见拉德纳巴德拉著《咱雅班第达传》和《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所列的《咱雅班第达行程表》,第62-64页。)
17世纪初,中国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爱新固伦),势力逐渐强大,蒙古东部科尔沁兀鲁思等几个部落归降后金。后金三征察哈尔国的结果,号称四十万蒙古大汗的林丹汗败亡,导致1636年内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封建主归附满洲,蒙古的势力大为消弱。新建立的清朝逐渐跟和硕特汗廷、喀尔喀三汗和部分准噶尔贵族取得了联系。清朝的扩张对卫拉特联盟和喀尔喀蒙古形成了直接的威胁,清朝的领土扩张和兵戎相见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此时对卫拉特和喀尔喀领土觊觎多时的沙皇俄国,开始侵略我国北部边境。他们对蒙古各部首领采取各种卑鄙措施的同时,还武力相加,侵占了不少的领土。他们在已占领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掳掠和驱逐当地居民,煽动内战,欲蒙古部落臣服于俄国,奴役蒙古人。面对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径,卫拉特和喀尔喀首领和人民坚决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斗争。他们武装反抗的同时毅然拒绝侵略者的政治、经济方面提出来的无礼要求,揭穿侵略者的种种阴谋,维护了领土和主权。但因各部尚没有同一的领导和共同御敌的行动计划,并且卫拉特、喀尔喀双方多年来因牧场、人口等诸多问题而造成的矛盾,一时无法缓和。
在来自外部势力的步步进逼,内部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不满时局的人民,以逃亡等形式反抗封建领主。因此,双方统治阶层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抵制这种情况的进一步蔓延。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深深的感到,加强各部之间的团结,巩固内部封建秩序,共同抵御外侮的重要性。《蒙古-卫拉特法典》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喀尔喀、卫拉特僧俗统治阶级共同制定颁布的。
二、铁龙年(1640)楚勒干以及《蒙古-卫拉特法典》的颁布
喀尔喀和卫拉特封建主们在准噶尔部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名和图克沁)和喀尔喀札萨克图汗素巴第(或者其子诺尔布)的积极倡导和共同努力下,1640年九月初(英雄铁龙年仲秋第五吉日),在塔尔巴哈台玛尼图渡口地方举行了楚勒干会议。会议由札萨克图汗为首的七鄂托克喀尔喀诺颜们和巴图尔珲台吉、额齐尔图台吉为首的卫拉特诺颜们和蒙藏黄教僧侣参加。占领青海的顾实汗和远在伏尔加河流域驻牧的和鄂尔勒克也率其二子参加了会议。
但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当中,没有一个资料证明,这次王公会议是如何筹备和怎样进行的。除了共同通过《亦克察济》(大法典)以外,无从得知其他的事项。从法典的内容来看,此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些很紧迫的问题。譬如怎样巩固政权、双方如何联合共同御敌、怎样处理逃亡问题、扩展领地等诸问题。《卫拉特简史》一书认为,“这次会议正处在顾实汗等人进军西藏的前夕,因此不能排除在这次会议上曾就进军西藏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并达成过某些协议的可能性”。(注:《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69页。)
这次楚勒干总共有多少人参加会议,尚不清楚。以前很多学者依据《蒙古-卫拉特法典》前言中提到过的署名,参加会议的有三位(一说四位)呼图克图,二十六位(一说二十七位)诺颜,共29位。迪雷科夫认为参加了32位诺颜和呼图克图。(注:迪雷科夫:《大法典——十七世纪蒙古封建法的古文献》,转引自马大正摘译,民族译丛,1984年5期。)法典前言中署名者是:参加会议的三位呼图克图,即恩振仁布齐(又称音赞仁布齐)、昂吉·合比·满珠室利、阿穆巴·希第·满珠室利。参加会议的喀尔喀和卫拉特诺颜依次是额尔德尼札萨克图汗(素巴第或诺尔布,不详)、土谢图汗(衮布)、乌巴什达赖诺颜、达赖洪诺颜、车臣诺颜、岱青洪台吉、叶勒丁诺颜、墨尔根诺言、额尔德尼洪台吉、戴本洪台吉、腾格里陀音、墨特池台吉、博额耶尔登、阿尤希哈顿巴图尔、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仑乌巴什、顾实汗、鄂尔勒克台吉、舒库尔戴青、额尔登台吉、岱青和硕齐、额齐尔图台吉、莫尔根岱青祖克尔、彻辰台吉、莫尔根诺颜、达马琳等。
目前学术界认为,在法典前言中署名的,只是当时有威望和有影响的人,事实上参加会议的决不止是他们,相当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法典前言中至少没有提到喀尔喀七鄂托克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卫拉特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有关咱雅班第达没有被署名,“因为当时他离开西藏到卫拉特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卫拉特的宗教活动刚刚开始,影响尚不大,所以未在法典前言中署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咱雅班第达应是参加了这次会议”。(注:《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68-69页。)有学者认为,被提名的这些二十九名宗教和世俗封建主都有全权代表的资格,而当时哲布尊丹巴和咱雅班第达还没有这种资格。(注:参见金峰:《四卫拉特联盟》一文,载《卫拉特历史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
法典的名称,自从帕拉斯搜集整理以来,很久一直没有固定的称呼。我们根据法典蒙文抄本前言中“都沁杜尔本二部诺颜制定了大法典”的记载,应称为《大法典》。另外巴图尔乌巴什图们所著《四卫拉特史》上也说“亦克察济”。想必当时把1640年的法典都叫做《大法典》。随着法典被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学术界有对法典有几种命名:
1. 《都沁·杜尔本大法典》,“都沁”(四十)指大漠南北的东蒙古,即蒙文史书所记载的“都沁图们蒙古”(四十万蒙古)“杜尔本”指卫拉特蒙古,即“杜尔本卫拉特”(四卫拉特)。蒙古文献习惯上“都沁·杜尔本”来泛称全蒙古。以前曾有学者把法典前言中提到的“都沁·杜尔本和叶尔(二部)的诺颜”(四十四二部的首领)一句错误的理解为,本次会议上参加了四十四名封建主或四十四部,(注:持这种观点的多为俄国早期研究法典的学者们,如列昂托维奇教授、戈尔通斯基等,他们的误解一直影响到梁赞诺夫斯基。)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被纠正。
2. 《喀尔喀-卫拉特法典》,因为这次会议是由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双方封建主联合召开的,所以有此称呼。
3. 《蒙古-卫拉特法典》,因为当时大漠南北的蒙古部落通称蒙古,为区别于卫拉特,喀尔喀单独也被称为蒙古。另外法典第一条“无论何人破坏此政权,如杀掠、抢劫大爱玛克、大兀鲁思,蒙古卫拉特联合起来,擒斩其身,没收其全部财产。擒杀者得其财产之一半,另一方两方共分之”条款来看,如此称呼也是合情合理。
4. 《卫拉特法典》,目前学术界普遍所接受的一种称呼。这是因为,一方面,此法典是在卫拉特的领地上制定的,从法典的内容看,比起喀尔喀地区,它较适用于卫拉特地区。另一方面,从法典制定之日起,卫拉特社会严格遵照法典来调整内外关系,自觉维护法典的精神。准噶尔汗国(政权)建立以后,成为国家大法,并有所更新。远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汗廷也一直使用此法典,并使其进一步发展。
5. 新《察津毕其格》,这是为区别于1640年法典以前的旧《察津毕其格》而命名的称呼。
6. 《1640年法典或铁龙年大法》,因为此法典是铁龙年(1640年)制定的,所以有此称呼。
7. 《卡尔梅克法典》,因为手抄本是从卡尔梅克获得,故有此称,国外学术界多有这样称呼。
三、法典的抄本、译本以及研究状况
蒙古民族的习惯法和成文法是研究蒙古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习俗的重要史料。法典最初应是当时通行的回鹘式蒙文书写的。(注:见戈利曼:《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的俄文译文和抄本》,载《蒙古文集》,莫斯科1959年版。李佩娟汉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1648年咱雅班第达创制托忒文后,才有了托忒文文本。回鹘式蒙文原文早已失传。法典的文本较多,差异也较大。率先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是俄国学者。
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参加1640年会议后,把法典带到伏尔加河下游,作为土尔扈特部众的法典。因而引起许多俄国学者对他进行研究和探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俄国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开端。当时一些学者或政府官吏到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据此写成一批著作,就土尔扈特游牧民族社会的历史、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都作了探讨和研究。巴库宁、米勒、菲舍尔和帕拉斯等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本主要有:
帕拉斯(pter simon pallas)《蒙古民族历史资料集》(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eoon volkerschften)一书德文版第一卷,第194-218页所载,1776年由德国约翰格奥尔格弗莱舍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1768年至1774年受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委托,赴俄国的亚洲地区考察研究。他在书中大量利用亲身调查材料,对当时留居于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人的历史、法律、社会习俗作了详尽叙述。他在卡尔梅克期间首次发现托忒文抄本,对法典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史料来源。邵建东、刘迎胜二先生以《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之名,翻译成中文。(注: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法典最早俄译本是1776年刊登在《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自由协会试作丛刊》第三卷上以《蒙古和卡尔梅克族法规译文》的标题发表。第二版是在1828年刊登在《北方档案》第2期和第3期上,以及刊登在同年出版的《祖国之子》第一册和第二册上。
列昂托维奇教授根据宾特科夫斯基的抄本,出版了俄文新译本:《古代蒙古卫拉特或卡尔梅克民族制定的法规》(《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古代蒙古卡尔梅克人或卫拉特刑法条例》)1879年在敖德萨出版。
戈尔通斯基教授俄译本:《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附噶尔丹珲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在卡尔梅克汗敦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民族制定的法规》,1880年,圣彼得堡版。戈尔通斯基对敦杜克达什补充法规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土尔扈特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时期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管理体系和宗教情况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尔梁德:《自上古至十七世纪的草原法》(1904年,喀山版)中介绍了法典。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部落之习惯法》所载1929年英译本;梁氏《蒙古习惯法之研究》所载青木富太郎1931年日译本。
195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整理了《卫拉特史资料(托忒文)》,以油印本的形式发行,其中就有《蒙古-卫拉特法典》和敦杜克达什法规的残本。
田山茂是专攻蒙古社会制度史的学者,其1954年出版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一书附录中,作者根据帕拉斯的德文译文,将《蒙古-卫拉特法典》和《敦杜克达什的补充法规》译成日语,并加以注释,这是日本对上述《法典》和《补充》的第一次完整的介绍。潘世宪先生在翁独健教授的推荐下,从1964年开始翻译,后因故辍译,最终1984年译成中文。因有些地方日译者理解错误而导致了汉译文本的质量。但对国内介绍法典和研究法典,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С. Д. 迪雷科夫:《大法典-十七世纪蒙古封建法的古文献》,1981年莫斯科版。他在这本著作中把托忒文本转写成蒙文,又翻译成俄文。对几种抄本和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且给学术界提供了很多信息。
科特维奇和戈利曼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肯定俄国有五种抄本。而迪雷科夫说,他就看到了四种抄本。俄国现有四种托忒文文本,一种保存在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全宗中;有三种保存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其中两种保存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一种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手稿库。科特维奇认为所有的抄本都是残本。他写道:“据俄国档案材料记载,在卡尔梅克诸汗牙帐附近札尔固帐幕内,保存了一份写在带花纹的白缎上的各种法规的全文,但是在卡尔梅克人内讧时期,这份法规已丢失,根据敦杜克达什说,他不得不在草原上到处搜寻法规的抄件”。(注:科特维奇:《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彼得格勒1919年第一册,《蒙古文集》1959年第141页。)
对此迪雷科夫认为:“绝不能从科特维奇的看法中得出:流传到现在的法典的卫拉特文抄本都是残本。相反,对这些抄本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有根据推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大法典》的几种抄本是《1640年法典》的全文。……事实上,除去呼和浩特有缺漏的文本外,所有四种卫拉特文抄本,都以同一项条款为结尾,该条款宣称,偷盗锅或三脚铁架应根据所盗物的质量罚盗贼一定数量的牲畜。要知道这些抄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副本,何况是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的。其次,在所有这四种抄本中,紧接着这项条款后都都是噶尔丹珲台吉的第一项敕令,只有两种抄本中没有他的第二项敕令。如果第197条款(迪雷科夫分成197条)的法典结尾已丢失,那么怎么会在所有四种抄本中保留的都是噶尔丹第一项敕令?在第197条款后,不曾有过其他任何条款”。(注:厄鲁特蒙古封建法的整理和研究,马大正摘译自(苏)迪雷科夫《大法典-十七世纪蒙古封建法的古文献(莫斯科1981年版)一书之绪论,民族译丛,1984年5期。)
新疆学者额尔德尼先生把托忒文本法典以《卫拉特大札撒》的名义刊登在新疆《汗腾格里》杂志1981年4期上,引起国内蒙古史学界的极大的反响。后1982年第4期《蒙古语文》杂志上转写成回鹘体蒙文。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墨日根巴特儿先生把该院馆藏托忒文文本转写成回鹘体蒙文。
道润梯步先生校对《汗腾格里》刊登的文本、墨日根巴特儿转写本和迪雷科夫转写本等三种文本,以《卫拉特法典》的名义校注出版。(198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道氏本虽然有些词句、历史事件等方面未免有误解和错误的判断,但到目前为止,尚认为是个较好的一种蒙文校注本。
宝音乌力吉、包格以道氏校注本做为蓝本,校注了《蒙古—卫拉特法典》,200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校注本只有几处词句上有新的解释外,并没有创新之处。
齐格先生编写《古代蒙古法制史》时,主要参考了道氏本外,还参酌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藏托忒文《卫拉特法典》。
笔者主要利用道润梯步蒙文校注本和《汗腾格里》刊登的托忒文本的同时参考了宝音乌力吉校注本。汉文译文主要参考齐格先生书外参酌潘世宪译文和邵建东、刘迎胜译文。
从18世纪末开始,研究者们对法典进行搜集、整理、注释、翻译各种文字。对法典的研究,俄国的学术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内对法典的研究较晚。清代学者虽然对西域历史、社会作过详细的论述并多部著作诞生。但卫拉特社会内部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却不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界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增多,国内也开始研究《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道润梯步、潘世宪、齐格、马汝珩、马大正、成崇德、白翠琴、马曼丽、冯时锡、罗致平、加·奥其尔巴特等学者从法典的史料来源、历史背景、性质、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分类、结构、制定者等不同的角度介绍和研究了此法典。
除此之外,语言学学者们从语言学和研究卫拉特方言目的出发,解释法典的有些字、词和纠正前人研究中的有些错误注释。这方面道·巴图扎布、布仁巴图、N·巴德玛、Q·巴图等学者作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纵观国内外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在历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去归纳、分类、剖析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是卫拉特法典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
蒙古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颁布的法典,对研究蒙古古代社会关系和人民的生活习俗提供十分可信的资料。充分利用法典所提供的资料,使史学研究更加完备。因为我们通常利用的编年史材料对社会内部情况等很少涉猎,它主要阐述蒙古地方与外界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法制史资料正好补充这一缺憾。随着民族法学和蒙古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卫拉特法典的研究会不断完善,进而取得更好的成就。
四、《蒙古-卫拉特法典》的主要内容
我们探讨1640年法典以前,肯定会涉及到帕拉斯《蒙古民族历史资料集》中记载的八条有关通奸(第1—4条)、财产分配(第5条)、侮辱行为(第6条)和妇女地位(第7、8条)方面的片断记载。旧《察津毕其格》约于15世纪至16世纪上半叶编纂,全文已失传,现在保存下来的,仅仅是帕拉斯片断记载。前面加旧字是为了同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相区别。其编纂年代,学术界持不同的看法。分歧的焦点是法典条款中的有关喇嘛教的规定。就是“与僧侣之妾通奸,完全不受处罚”一条。
卫拉特地区何时传入黄教,目前尚未明确。卫拉特毗邻的东蒙古地区16世纪后半叶开始佛教的传入,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卫拉特地区。据托忒文文献,大概是卫拉特联盟盟主拜巴噶斯1616年召开的一次楚勒干上,决定引进藏传佛教。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有西藏僧人在卫拉特地区活动。因为,1604年被请到喀尔喀的察干诺们汗(又说迈达里呼图克图)不久就到了卫拉特。史料证明,1616年楚勒干上卫拉特诺颜们决定引进黄教时,他已经在卫拉特了。(注:巴图尔乌巴什图们著:《四卫拉特史》(托忒文)。)
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时,除了黄教以外,还有其他的派别也到蒙古地区传教。所以传播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红黄之争”。萨迦、噶玛等红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而黄教的教规是决不允许的。佛教传入蒙古以后的几个世纪的发展情况来看,黄教寺庙集团严禁喇嘛娶妻生子。但有意思的是,1640年法典中也有一条“骂成家的班弟,罚一马,动手打,罚双马”的规定。所以旧《察津毕其格》的有关喇嘛教的规定是比较可信。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前期,蒙古喇嘛可不可以娶妻,值得一研究。
列昂托维奇教授认为,旧《察津毕其格》是卫拉特联盟形成初期的产物,在15世纪制定和颁布的。(注:转引自梁氏《蒙古法基本原理》,第50页。)田山茂认为是:“15世纪到16世纪前半叶”。(注: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231页。)齐格先生认为,田氏判断有误,应该是1616年以后,因为这个时期黄教尚未进入卫拉特地区,有关对僧侣的规定不符和时代。(注:齐格著:《古代蒙古法制史》第111页。)冯锡时教授和成崇德教授等学者认为,约于15世纪至16世纪上半叶编纂。(注:《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284页,成崇德:《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第45页。)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这样分期比较合理。因为所谓的旧《察津毕其格》并非1640年法典那样就通过一次楚勒干来制定的,而是元亡后,卫拉特的统治者们在几次的卫拉特联盟形成过程中陆陆续续的制定和颁布的。
法典大部分内容是蒙古社会古来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内容。跟《阿勒坛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的相关条款相比较,有些内容基本相似。《阿勒坛汗法典》也禁止揪别人的头发,规定“男人揪妇女头发者,罚牲畜五九”。旧《察津毕其格》规定:“卡尔梅克人格斗时,乱揪别人的辫子便构成犯罪。因为辫子属于王公所有,是表示恭顺的象征。但是,如果是没有梳成辫子的头发,谁揪也不受处罚。因为没有梳成辫子的散发是属于个人的并不视为王公所有”。蒙古以前的法典中虽有不准揪别人的辫子的规定,但为什么这样会犯罪,并没有作出解释。而旧《察津毕其格》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已经“梳成的辫子的头发”,实际上是代表人身依附关系,“没有梳成辫子的头发”是不受法律保护。
法典规定的有关通奸方面的内容,比起成吉思汗《大札撒》和《图们汗法典》宽容许多。对此不少学者为法源问题而伤脑筋,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有些落后的、野蛮的、稀奇古怪的陋俗会被时代所淘汰和摈弃。除僧侣之妾通奸不受处罚外,法典规定“与王公的夫人通奸被抓住时可拿出牝山羊及山羊羔各一只作为赔偿;一般通奸,奸夫拿出四岁马一匹给奸妇之夫,奸妇应拿出三岁马一匹给审判官;捉到私自跑到自己女奴隶那里来的人,可扣留他所带的钱、马及其他一切持有物之后,予以驱逐。女奴隶不受处罚”。
对子女的财产分配方面,法典规定“青年人可以长到自己可以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时,立即脱离他父亲的权力控制,按照他的要求分给一部分畜群,去过完全独立的生活,可以直接为王公服务”。蒙古社会自古就有幼子继承父亲的大部分财产,留居其身旁共同生活外,其余子女都另立门户的规定。
蒙古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是,依法保护妇女的地位。这是游牧民族社会中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所起到的地位有关。蒙古妇女一方面,经济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她们法律上受到保护。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农耕社会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游牧法与中华法系法典的区别之一。法典规定“妇女如果坐帐蓬里自己的坐位上(即入门的右侧、灶炉的后面、家长卧床跟前的座位)的话,她骂客人,甚至向客人投掷柴块或家具,谁也不能用手触及她;但是,这个妇女如果是在争执中一旦离开她的座位,走出帐篷,这种特权便消失了,她对客人的打骂便应受处分罚;妇女到王公跟前请求免除自己或其家族的处罚时,从尊重妇女的原则出发,轻罚一般全免,重罚减半”。
旧《察津毕其格》的有些内容还反映在1640年卫拉特法典当中,有的在实际生活中已有修正或废止。
1640年法典原文没有分条款。因此,研究者们按照内容的区别和自己的理解,把法典的原文归纳若干项和分若干条款。帕拉斯德文版把它分为130条,列昂图依契俄文本分为150条,戈尔通斯基俄文本分为121条,道润梯步先生蒙文校注本把它分为120条。宝音乌力吉和齐格遵循道润梯步条款。道氏把法典的内容分成27项,齐格分成26项,宝音乌力吉等分成34项。
《蒙古-卫拉特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的内容特别丰富,涉及面之广,蒙古族任何一个时期的法典无法比拟。他是17世纪中期蒙古、卫拉特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了解卫拉特社会生活的一部辞书。
《法典》的法源大体上相沿古代蒙古社会一直遵循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以及《图们汗法典》、《阿勒坛汗法典》、1639年前的《喀尔喀七旗法典》等成文法和法典中经常出现的“以前的法典”,即旧《察津毕其格》。法典是在这些法律文献的基础上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而编纂、制定。
《法典》一开头就有一首赞美佛教,虔敬叩拜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以及黄教两位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赞美诗。然后祈求参加本次会议的恩振仁布齐呼图克图“为众生做成善业”。这无疑是17世纪蒙文文献的一种编纂模式。这足以说明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深入和广泛所接受。第二段记述了参与本法典的四十四二部29名僧俗官员。第三段开始进入正题,即法典的有关行政、民事、刑事、宗教、诉讼、审判以及相应的处罚条款。
(一)有关蒙古、卫拉特内政以及调解各部关系的规定
1636年,漠南蒙古归附清朝以后,蒙古的政治中心自然而然转移到了漠北和漠西。这种情况并不偶然,因为在此之前,蒙古各部在内政外事上相对独立,并且各部间也有历史上酿成的不同程度的旧隔阂、仇恨和新矛盾。林丹汗的败亡,漠南蒙古的归附清朝,对喀尔喀、卫拉特封建主们来说不得不思考的新问题。于是双方感觉到了政权巩固的重要性。
1640年蒙古、卫拉特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巩固政权,调解内部关系和矛盾,一致对外。这是双方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法典特别强调对破坏政权方面的内容。规定“无论何人破坏此政权,如杀掠、抢劫大爱玛克、大兀鲁思,蒙古、卫拉特联合起来,擒斩其身,没收其全部财产。擒杀者得其财产之一半,另一方两方共分之”。
双方以法律的形式不能无端的互相“争夺边界,进入小爱马克或和屯”。若违犯“罚铠甲百领、骆驼百峰、马千匹作为赔偿,并应归还所掠之物”。并且有公务的人的处罚比平民严。共同御敌,防御可能发生战争的事情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双方规定,当大敌当前时,一定要互相通报敌情的责任。对明知通报而没有出兵的相邻部落的大诺颜,处罚铠甲百领、骆驼百峰、马千匹作为赔偿;如果小诺颜不来,处罚铠甲十领、骆驼十峰、马百匹。若入侵者是大规模的敌人时,不通报的话,受到“永远流放其子子孙孙,斩杀其人,夺其一切”的严厉惩罚。而不通报一般强盗来犯,仅没收其一半的牲畜。
发生骚乱(包括外敌侵略所造成的骚乱和内部骚乱)时,集合到诺颜处,听到消息而不来,受到前面提到条款惩罚。如果路远而造成的迟到情况,酌情处理。对放走强盗而造成的损失,不同阶层的人负有不同的责任。法典规定“谁放走强盗,没有追回被抢的马群,罚没其牲畜、财产的一半。如死了人,按照习惯顶替。追回的人死,由丢失者之兄弟以一别尔克顶立。看见、听到而不追赶,如是赛因库蒙,罚分其牲畜、财产之半;如是顿达库蒙,罚一九;如是毛库蒙,罚一五。
1640年会议上解决的还有一项重要议题是有关逃民问题。17世纪卫拉特联盟内讧时期和喀尔喀卫拉特双方战争时期,很多部落为逃避战乱,移居到它处。这一问题一直是双方的敏感问题,若不合理解决会影响双方的联合和导致新的矛盾的出现。
为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双方协商后得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从火蛇年(1617)到土龙年(1628),在蒙古的巴儿虎、巴图特、辉特已被蒙古融合,在卫拉特的已被卫拉特融合。此外之人,该归喀尔喀的归喀尔喀,该归卫拉特的归卫拉特。如有人不予归还,按占有之人数计,向占有者每人罚马二十匹、驼二峰,连同占有者本人一起归还所属方。与却图(注:却图,史称楚库尔却图台吉或库苦诺尔却图汗。是喀尔喀格埒森扎的第三子诺诺和威征的第五子巴阿赉子,生于1581年。在喀尔喀地区积极推广黄教,后因政见不同而导致喀尔喀内讧,率领部众迁居青海,占领青海,1637年被顾实汗的卫拉特联军打败身亡。他曾支持红教,联络林丹汗、臧巴汗、白利土司,建立四方联盟,共同对付黄教势力。林丹汗的败亡,这一计划受到挫折。)一同进卫拉特的人如逃回喀尔喀,要归还给卫拉特”。
进而双方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和避免接受对方的逃亡者,规定:“不论谁那里来了逃亡者,罚其财产、牲畜之一半。然后送交其主人。如逃亡者杀了人,以大法罚畜八九,给证人一九。如收容之诺颜作梗阻拦,不听处罚、不给牲畜,罚此诺颜铠甲百领、驼百峰,卫拉特、喀尔喀平分。”
也就是说,由一方诺颜下逃出投奔另一方,应当送还;从喀尔喀逃出的投奔者应给还喀尔喀;从卫拉特逃出的投奔者,应还给卫拉特。双方亲属也应彼此送还逃亡者。《法典》还规定:“从别人那里来的人,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其投靠的诺颜如给其生活资助,要给他靠本人劳动所得牲畜的一半”。如杀外地寻名而来的逃亡者,罚五九。如送还给其主人,有几个箭袋要几匹马。如抓捕外逃的逃亡者,除其人外,其财产、牲畜对半分。如根本不交出逃亡者,以法惩处。其真假要通过证人证实。如无证人,逼审其爱马克首领。
(二)有关保护黄教方面的规定
蒙古、卫拉特联盟皈依黄教后,先后都依法取缔了萨满教,积极推广黄教。萨满教受到限制,黄教利益受到法律保护。
《法典》规定,谁如请乌都干(女萨满)、孛额(男萨满)做法事,没收邀请者之马和罚来做法事的乌都干的马,看见之人如不依法没收,罚他的马;谁如看见翁供,要取走,其主人如拦阻不给,罚要他的马。萨满行巫诅咒上等人,罚一五;诅咒下等人,罚马二匹;以黄鸟、阿兰雀、狗等行咒,罚马一匹;以阿拉克山之蛇、其他种类之蛇行咒,罚箭二支。如无箭,罚刀一把。
相反,黄教僧侣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若违犯法律规定,不管是汗、洪台吉都受到惩罚。规定“如杀掠、抢劫寺庙喇嘛所属爱玛克,罚铠甲百领、驼百峰、马千匹,更有特殊者处罚伊克黑卜。”目前学术界对“伊克黑卜”是何等程度的处罚,尚未弄清。
喇嘛阶层有特权,他们不缴纳赋税,汗、诺颜等不能向他们征用乌拉。法典规定“向喇嘛、班第们征用乌拉骑乘,罚牛一头。骑用栓有敬佛鬃尾的马匹,罚一马。如系乌拉赤抓给的,所罚之马向乌拉赤要,如系使者自己骑的,向使者要”。
《法典》还规定,骂绰尔济等,罚九九;骂诺颜的巴克什喇嘛,罚五九;骂格隆,罚三九,动手打,罚五九;骂乌巴什、乌巴三察,罚马一匹,动手打,根据打之程度处罚。僧侣受到保护的同时,他们的属民(沙比纳尔)也受到比其他人特殊的保护。规定,危害或杀戮喇嘛属下的上等人,赔五个人;下等人赔两个人。然后法典的制定者们,很有把握地说“没有人违犯此条”。
这充分说明,黄教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有效的控制住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谁人违犯此规定,大诺颜罚驼十峰、马百匹;墨日根、岱青、楚库尔一级别的诺颜,罚驼五峰、马五十匹;小诺颜罚以驼为首的三九牲畜;塔布囊、执政的四图什墨尔,罚以驼为首二九牲畜;各鄂托克的赛特、图什墨尔罚以驼为首一九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