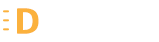万里雪飘的冬天作文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作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
万里雪飘的冬天作文
入冬的感觉分明已经贴近眉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大概是过于麻木了,我丝毫没有感觉。走在大街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穿上御寒的大衣,我才恍然,入冬了。
最近在心里总是郁郁慌慌的,坐立不安。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我的思绪已经被窗外飞过的小鸟衔走,带回故乡老屋,领到山脚下新添的坟前。
我不是记恨的人,不懂得如何去长久地憎恨一个人。所以我会为他落泪,一把鼻涕一把泪。
上音乐课的时候,那个笑容如莲花开落的老师让我们齐唱《懂你》,我的双手顺从地搭在钢琴键上,刹那间忽然觉得有气无力。当大拇指按下去的时候,中指飞快地下意识按下……十指尖泻下熟悉的旋律,他们穿着整齐,一脸灿烂地唱:“……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多想靠近你,告诉你我其实一直懂你……”十指突然一阵剧痛,眼睛开始疼得直涌眼泪。“当!”的一声,我重重地伏在钢琴上,莫名地失声痛哭。
前几周考语文的时候,没有来的一阵忐忑不安。刚笔写到一半突然断水,当下慌了起来。那种不安之感霎时冲上心头。在那时大抵就隐约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爷爷走得很突然。
老屋的砖墙看上去又碾过一层白灰灰的尘埃。斑驳的树影摇曳在院子里。四下里很沉静,平日里好吠的狗在此刻也安静下来。我不喜欢这种近乎压抑的气氛。于是走出老屋。外面的阳光很灿烂,刺得我眼眶直溢泪珠。
爷爷入土那天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窗外阳光明媚,但我内心却溢出阴霾。我痛苦得无法呼吸。仿佛有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把我罩住,没有一丝风可以透进,完全与外界彻底地隔绝。我试图与外界各隔绝。热闹是属于外面的,我什么也没有。
我在忏悔。我似乎从未正眼看过爷爷,见了面既不打招呼也不微笑示好。我总是下意识把他全全透明化,无视他的存在和关怀。我甚至公然甩开他握着热水杯的手,把盈载他对我的关切的温水洒在地上,杯子碎成片,亮晶晶地折射出我狰狞的面孔。心里蓦地一阵抽痛,我竟然没有叫他“爷爷”,一次也没有。
冬日的阳光很淡,没有夏日的毒辣,很暖很窝心。那些阴柔的光线照在我惨白的脸上,酥酥地,像母亲的手温和地抚摸着我的脸。其实我知道这些都不能驱散我内心的阴霾。它们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田上,稍稍拔出,我的心就会痛得直流血。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了解爷爷,甚至连他的生日、嗜好的都不知道,也没过问。我不好奇他喜欢什么憎恶什么,而只好奇怎么打扮才能让自己更出众。爷爷蔑视我这好奇。他总是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可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个人礼节的最好体现。于是我们之间不停的为此吵架。
我一直深信不疑爷爷不喜欢我。那些出奇相似的话语捻断了我对他的好感。而我,似乎也感觉到了他对我怀着浓烈的敌意。
母亲说,当年他得知生下来是女孩,便多次暗示遗弃她。母亲没有应允,他毒辣的目光此后如影如随,终于没忍住和我的父母翻脸;外婆说,我三岁的时候,某天由他接回家。过马路的`时候,他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走,把一个三岁无知的孩子完全忽略在车辆纵横的马路上。若非一个老奶奶看不过眼,左手牵孙子、右手紧拉着素不相识的小女孩,顺利走过那一条条斑白的横线,我或许早为殇了吧;街坊的三姑六婆每次见到我,总会紧紧拽着我的手,嘘长问短,而他,却从未这么做。她们于我,只是邻居,却仍旧关怀我;他于我,是缕不清的血缘关系,却一直被他搁浅在遗忘的角落,自生自灭。这真真可笑,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奋力反抗他、处处与他作对。
他叫我回老屋吃顿饭,我答应了,却没有去;他劝我要好好学习以便长大找份好工作,我冷笑,说,即便找到好工作也不要指望我养你;他信手拈来教育我,我总是一把推开他,径直跑开……太多太多的冷漠,我把他一次次地中伤。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我竟然冷笑。
爷爷老了,在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下,迅速地苍老。两鬓白霜染透,一脸皱纹爬满,刻尽了沧桑。还有那双失神黯淡的眼眸,褪去生机叹沧桑。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中秋时节。老屋热热闹闹地聚集了一大帮人,谈笑风生。爷爷生性好静,只喜欢一个人在院子里赏月乘凉、缅怀老早撒手西去的奶奶。那晚我无意走进后院,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爷爷。月华洒在他沧桑的脸上,眉间有着隐隐约约的无奈。我可以很分明地读懂他眼中的无奈。年老,被遗弃,孤独。曾经不可一世的他,刹那间,便踽踽一人。那凄凉的身影被月光拉得长长的,颀长的背影在我脑海中不可磨灭。他也有曾经,只是,岁月蹉跎,我们都忘记了。他也是可怜的,颤颤巍巍的步伐,瘦小的身躯。老了,他终究还是会老的。
那时我其实已心生怜意,多想过去为他披上一件御寒的大衣。可是我最终并没有那么做。或多或少因为羞涩,抑或不愿让他知道我早已释怀他的重男轻女。我终于还是错过了冰释前嫌的机会。花开一次就成熟,我却错失了;而错过的花季,不再属于我。
细细想来,有时也觉自己可笑,似乎踯躅在十三、四岁的阶段,叛逆地伤害着别人,同时也伤害着自己,面对白昼生出刺来,面对黑夜淌出血来。
二叔把门打开,告诉我爷爷已经入土为安了。我点点头,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说到,你还记恨着么。我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早就忘记什么是恨了,我现在只讨厌自己的不懂事,无端耍性子。
我来到后院,抱膝而坐。我终究不会原谅自己。我记起奶奶走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爷爷脾气不好,你要学着迁就他,他要发怒了,就真的会狠心重重地抽你一耳光。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爷爷总是迁就我。只是为我的颓废而刮了我一巴掌。可是现在想起来,那个耳光很轻,一点也不会感到痛。爷爷并没有用力打我,只是温柔地碰了我的脸颊一下而已。我真后悔自己那时居然冲他大吼一声:“我恨你!”。此时耳畔边充斥着那句话,仿佛在讥笑我的愚昧。猛然想起前几个月身子虚弱的爷爷对体型魁梧的四叔暴打了一顿。那粗粗的枝条深深地烙在四叔的胳膊上。那是我第一次见亲眼目睹爷爷面孔扭曲地发脾气。仅 其实那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甚至天真地以为他嗜钱如命。
要不是三叔和二叔的争执声惊动了我,爷爷在我眼里仍旧是那个矮矮的、瘦瘦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吝啬又自私。三叔在前院大吼,凭什么把爸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她!她不是最恨爸的么。然后就听到二叔的声音,爸的遗书里就是这么交待的,你忘了三弟被爸毒打的事情了么,三弟挪用的正是爸省吃俭用攒下来给朵朵的钱,所以爸才会发这么大的火。我的耳朵里“嗡”的一阵尖啸,像被人打了一棍子,摇晃了一下,有些站不住。那是怎么样的感觉,复杂难叙。我“哇”的一声,第一次为爷爷哭得肝肠寸断,在后院歇斯底里。
真相若是这般残忍,我情愿我永远苟且在谎言中。
前几天打开电视,碰巧逢上S.H.E在唱《候鸟》。从电视机里缓缓吹出歌声。彼时初冬的阳光正好,斜斜地透过落地窗户,映照出我的苍白以及悔恨。我仿佛看到爷爷站在被树丛隔离想念的河岸边,默默望着北边——你的爱飞很远,像候鸟季节变迁,你往北向南说再见。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但泪线很顺畅。
爷爷走的时候面含笑容。听医院的护士说,他临终前反复在交代遗产的归属。于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人是我。于终后,在初冬的阳光下怀念他的人还是我。